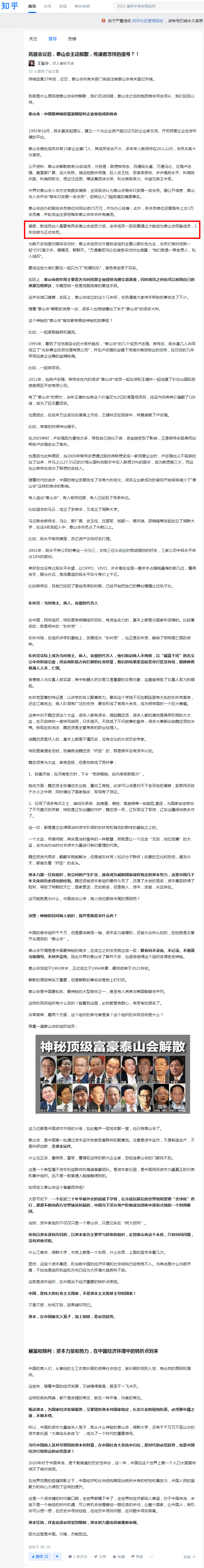今天的狄俄尼索斯神庙比较热闹,“…♩…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自咱的手…♪…”
而阿芙洛狄忒神庙也很热闹,“…♫…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…♬…”
克勒贝尔广场两端的宏大叙事,你方唱罢我登场,交相辉映。
“现在的神棍真没素质”,恩佐・略绿正在喂鸽子,“最恨这帮公共场合外放管风琴的傻哔”。
“是巴扬”,路人甲纠正,“真巧吖,你也在喂鸽子”。
“巧?也?”恩佐听着奇怪,“这里的鸽子很常见?还是很不常见?”
“你是新来的吗?”路人甲反问,“不知道广场规矩?”
“啥?”恩佐更奇怪了,“我就过来转悠一圈散散步,闲得蛋疼喂鸽子玩,坏了啥规矩?”
“唔,看来是误会了”,路人甲自我介绍,“吾乃缪斯公会零级吟游诗人,花名‘月之珊瑚’”。
“碍着你们耍把式卖艺了是吧?”恩佐一时红色液体上头,想起自己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,勉强忍了下来,决定先顺口胡诌套近乎,“看来是同行,我是游吟诗人,没加入过什么公会,花名‘鸡撕兔’”。
“用不用我帮忙介绍?”月之珊瑚似乎对于陌生人没有最起码的警惕感,反而殷勤的搭话,“入会需要三个介绍人,组织考察一年”⑦。
“不必了”,恩佐拒绝,“我又不是孤魂野鬼”。
“譬如行脚僧,晨起打包轻①”,月之珊瑚念了两句诗,“那么师兄云游至此,准备在何处挂搭?”
“开门拂榻便酣寝,我是江南行脚僧②”,恩佐也念了两句诗,“已有落脚之处,不劳师兄挂念”。
“本来你想唱哪段?”月之珊瑚不想打哑谜了,“不知道今天两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撞车了吧?”
“波洛夫大队人马从顿河,从海边,从四面八方⸺来了!③”恩佐明白“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”的道理,不拿出点干货出来,这位自来熟的路人甲不定会干出点啥来。
“一点也不合辙押韵”,月之珊瑚嗤之以鼻,“典型的翻译腔”。
“Рускыѣ пълкы оступиша.
”,恩佐先念原文,再翻译成当代法语普通话,“罗斯军被围。”
“嗯?”月之珊瑚出乎意料,“想不到你们还需要在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上下功夫”。
“Дѣти бѣсови кликомь поля прегородиша, а храбрии русици преградиша чьрлеными щиты.
”,恩佐接着念,然后自行翻译,“鬼子兵喊声震天,四面包抄;罗斯勇士用红色盾牌阻挡。”
“原来是抗鞑神剧”,月之珊瑚恍然大悟,“最近这套样板戏挺流行的嘛”。
“现在你们鞑语学不好,也就少挣几个钱”,恩佐不念了,假惺惺的板起一张悲天悯人脸做语重心长状,“但是当年,没考过鞑语四级的同志,都牺牲了”。
“呃……”月之珊瑚一时语塞,以前还从来也没意识到这简简单单的一个“鞑”字,其内涵与外延,所指与能指,褒义与贬义……竟然恐怖如斯?!
“毕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”,恩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一黑黑仨,诡道兵家理念运用大成功,心里暗爽,决定见好就收,于是转移话题,“说起来,这俩神庙如此热闹,广场上就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,那么平时你们怎么出摊儿呢?”
“也就偶尔有人包场”,月之珊瑚也知趣的转移话题,“都是古典式建筑,拉个横幅搭个顶棚摆满花篮,打扮成啥样的都有”。
“我说嘛”,恩佐语气开始亲切了,指着阿芙洛狄忒神庙⸺其实是神坛⸺的方向,“来之前听说过地标建筑黎明宫,刚才还奇怪啥时候拆迁了”。
“咳,也不是经常如此”,月之珊瑚顺口搭话,“谁家闺女嫁了个色目人,一定要大办特办,说是兜里不差钱儿”。
“那边呢?”恩佐指着狄俄尼索斯神坛方向坚决贯彻落实“入太庙,每事问④”的最高指示精神,“唱对台戏的?”
“你说红房子吖”,月之珊瑚作为地头蛇,对地面上风吹草动鸡毛蒜皮都很熟悉,“那是捧场的,负责提供‘红红的高粱酒’顺便打广告”。
“噢……”恩佐扮出醍醐灌顶的表情,“看来平时的噪音污染并不严重”。
“即便庙里面的管风琴外放的时候也没这么洪亮”,月之珊瑚解释,“这是单独请了乐团在外面放”。
“竟有这样的事?”恩佐睁大眼睛,额头亮晶晶的,“管风琴还能搬来搬去?”
“刚才跟你说了嘛”,月之珊瑚很不高兴,或者说很高兴,“那是巴扬,你当成便携管风琴理解也行”。
“原来如此”,恩佐扮出恍然大悟的表情,“我就说音色怎么如此饱满,音域怎么如此宽广,真不愧为宏大叙事”。
“配合史诗服用更佳,比如你念的那种”,月之珊瑚插播广告,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,商家让利打折到底,精彩不断优惠连连,只要一千五百杜卡特,机会只有一次,人生不可重来”。
“我买不起”,恩佐直说了,“一千五百杜卡特的解决方案,吓着我了”。
“呵,穷哔”,月之珊瑚嘲笑。
“腊汁猪肉火烧一个,咖喱牛肉饭一盘,羊肉泡馍一碗,照烧鸡盖饭一份”,恩佐把菜谱上招牌主食都点了。
“就您一位?”侍者听着奇怪,“本店货真价实,从不缺斤少两”。
“啊,就我自己”,恩佐说,“放心吧,能吃完,不会糟践东西”。
“您好大的饭量”,侍者恭维,正常做成一单生意当然没意见。
“人是铁饭是钢”,恩佐解释,顺口拉家常,“先垫垫,一会儿有个酒局,吹牛哔的时候也有力气”。
“请慢用”,侍者听懂弦外之音,不要酒水,于是送上一壶免费茶,一碟开胃菜。
恩佐继续研究菜谱。
“这位客官”,侍者走向门口,“进店请脱帽”。
“又不是礼帽”,来人头戴软帽,“黎塞留阁下看得清我这张脸”。
“那也不行,总有人检查”,侍者解释,“请您体谅一下我们的苦衷”。
来人无奈,摘下帽子揣在兜里。
侍者一愣。
恩佐好奇,扭头一看,那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正中,有个清晰的脚印,深达寸许。
“笑什么笑?”来人看着恩佐,有些恼羞成怒气急败坏,“没见过垫脚石么?”
“不是绊脚石?”恩佐反问,脸上笑容不变。
“不是!”垫脚石看恩佐一点不怂,索性走过来坐在桌子对面,招呼侍者,“这位点的餐,原封不动给我来一份”。
“你不问问我点了什么吗?”恩佐看垫脚石态度强硬的伸手示意想开口解释的侍者闭嘴,就问了一句。
“不用问”,垫脚石气哼哼的,“咱俩前后脚进门,正好两份一起出锅”。
侍者看恩佐没再说啥,就直接开票送去后厨了。
俩人沉默的喝茶吃菜,听着后厨轰鸣。
“这么多?”上桌的时候垫脚石才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。
“您好大的饭量”,恩佐嘲笑。
“彼此彼此”,垫脚石不示弱,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敞开肚皮吃干抹净,输人不输阵。
“糟践东西可不好”,恩佐进餐速度极快,唏哩呼噜吃完,喝茶消食,看着垫脚石板起一张愁眉苦脸做骨鲠在喉状,开口讽刺。
“高,实在是高”,垫脚石竖起大拇指称赞恩佐,“好饭桶”。
“确切的说是饭筲”,恩佐纠正,不以为耻反以为荣,“索邦头号酒囊饭袋的鼎鼎大名,巴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?”
“请问可以收桌了吗?”侍者看垫脚石结账走人之后,恩佐还是坐着不动闭目养神,就问了一句。
“啊,可以,结账吧”,恩佐睁眼,“吃撑了之后就容易犯困”。
“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吗?”侍者看恩佐结了账之后还是瘫在椅子上眼观鼻鼻观心,看情况很快就要打呼噜了,又问了一句。
“啊,不用了”,恩佐睁眼,“主食吃多了也容易犯困,我在这里坐一会儿不碍事吧?”
“那请您把行李挪一下”,侍者提醒,“很快就到饭点了,店里的顾客会比较多”。
恩佐欠身伸手企图拿桌边行李,够不到。侍者见状伸手试图帮忙。
“一千五百格罗索呢”,恩佐说,侍者连忙缩手。
恩佐的屁股终于离开椅面了,抓过行李往旁边墙角一扔,箱内发出和谐的一阵轰鸣。
“已经坏了”,恩佐看侍者惊讶,就解释了一句。
“是要送修吗?”侍者忍不住问。
“不”,恩佐懒得解释,“留作纪念”。
恩佐消食完毕出门,拎着行李沿街溜达,发现前面小巷入口聚集了不少人,有条子有神棍还有围观群众,一时好奇就走过去看热闹。
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子趴在地上,脸浸在一处水洼当中,大约的确是死了⑤。一个大眼珠子飘在之上一人高的地方。
“看够了吧?看够了吧?”条子开始撵人了,“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”。
“有啥公务?”有群众质疑,“不就是清理背街小巷撵吉普赛人么?”
“穷家帮专项整治行动”,条子纠正,“都是些小偷、妓女、乞丐,你们也深受其苦吧?”
“还有算卦婆子”,有人民补充,“还有杂耍矬子”。
“土耳其人终于要滚蛋了”,神棍放话了,“没人罩着他们了”。
“那死个孩子算怎么回事?”群众质疑。
“没准是《太阳报》狗仔队摆拍呢,一会儿就该有‘家属’闹丧了吧?”条子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流氓无产阶级以及其背后赞助商,“挺着大肚子卖巧茶的你们又不是没见过,采生折割专业户弄死个孩子司空见惯”。
“大眼珠子看见了?”人民质问。
“就是没看见才有人报警的”,条子解释,“监控密度还是不够”。
“写个六行字就能被找个茬绞死的时代”,群众发牢骚,“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”。
“黎塞留阁下一退休”,神棍摇头,“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”。
“该超度往生了”,条子提醒,“我敢肯定,这个棚户区里面一定有亡灵巫师”。
“我只会净化”,神棍摊手,“他们又不信我主”。
“还没结案呢”,条子有不同意见,“现在还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”。
“他们信什么?”神棍环视四周,看见有年迈的两口子望之不似羔羊,就伸手一指,“你俩,按你们规矩做个法事”。
“我们是真正的埃及人”,杂货铺店主老头解释,“不是吉普赛人”。
“那也差不多了”,神棍惦记着赶紧搞定收工,“反正都是一回事”。
“我试试吧”,杂货铺老板娘老太太看着心里不落忍,征得神棍和条子同意之后,上前把尸体轻轻的翻过来。
孩子脸上是一幅死不瞑目的狰狞表情。
老太太开始吟诵:
恩佐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出现了,就在四周飘荡。
抬头,天上似乎有鸟人降临。看神棍的反应,应该也感觉到了。
聚精会神凝气于目,盯着那小孩子,能看见半透明的人形似乎正在脱离尸体。
鸟人要扑上去?
神棍的手拢在袖子里,暗中搓动十字架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。
鸟人散了。
又有一拨鸟人?头上长角?
围观群众当中有个家伙的手拢在袖子里,捻过一颗佛珠。
鸟人又散了?
还有什么?无定形的东西。
围观群众当中又有个家伙的手拢在袖子里,顺时针扫了一圈太极八卦图徽章。
也散了。
然后出现的是比蒙、利维坦、猛犸还有其它不知名的传奇怪物。
没人管?
恩佐的手揣在兜里,捏住大卫之星徽章,拇指点在正中间的「卐」字中心上。⑥
果然散了吧?
神棍扭头看了恩佐一眼。
孩子的面部表情已经变得安详,眼皮也合上了。
老太太吟诵完毕,看着孩子发呆,忽然把尸体抱起来,紧紧搂在怀里,放声大哭。
“这位裁官大人,掏钱吖”,恩佐看神棍无动于衷,忍不住开口提醒,“是你请人做法事的”。
“又不是我自己做法事”,神棍拒绝,“走不了账不能报销”。
“那好吧”,恩佐把行李递给杂货铺老板,“如果你自己能修好的话,送到当铺怎么也能换个一千五百第纳尔回来”。
条子盯着恩佐。
“看什么看?没见过败家子么?”恩佐放下一句场面话,扭头就走,人群分开,让出一条路来。
“喝酒去!”恩佐大吼,每走一步,石板路上都留下一个脚印,深达寸许,“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!”
(完)
- ① 清・赵翼《秋园预治敛具诗以调之》
- ② 宋・陆游《双流旅舍》
- ③ 古东斯拉夫语汉语对照《伊戈尔出征记》,李锡胤译,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- ④ 《论语・八佾》
- ⑤


- ⑥
Raëlism or Raëlianism
- ⑦